第一章 芒种
我是在芒种那天进的青棠村。
山雾裹着蝉鸣漫过青石牌坊,牌坊上"青棠"二字被雨水泡得发涨,像两团化不开的血渍。村口老槐树下蹲着个裹蓝布头巾的老妇,见我背着相机过来,突然用拐棍敲了敲地面:"女娃子,莫往村东头走。"
我蹲下来和她平视,她眼角的皱纹里爬满蚯蚓似的青筋,"婶子,我是来采风的,听人说你们村有老变婆的传说?"
老妇的手猛地抖了抖,拐棍"当啷"掉在地上。她弯腰去捡时,我瞥见她后颈有道暗红的疤,像条扭曲的蜈蚣。
"莫提那三个字!"她突然尖声起来,声音像刀刮玻璃,"三十年前的事,还不该烂在土里?"
我捡起她的拐棍递过去,指尖触到她掌心的老茧,硬得硌人。她却像被烫到似的缩回手,倒退两步撞在槐树上,树皮簌簌落下来,盖住她脚边一个褪色的红布包。
那天夜里,我在村口的"山月民宿"落脚。老板娘是个圆脸妇人,四十来岁,腕子上系着串檀木珠,见我拖着行李箱进来,眼睛弯成月牙:"姑娘可是来写生的?我们青棠村山清水秀,最出片子。"
我应和着,把相机镜头盖搁在柜台上。她端来姜茶时,袖口滑下去,我瞥见她手腕内侧有道月牙形的疤,淡粉色,像枚褪色的唇印。
"夜里不管听见啥动静,千万别应。"她往我枕头底下塞了把剪子,铁锈味刺得鼻尖发酸,"要是有东西摸你窗户,用剪子戳。"
我笑着应下,等她出了门,摸出手机给同学发消息:"青棠村的恐怖故事素材有着落了,这老板娘够神秘。"
后半夜雨下得急,瓦片上的水声里混着指甲刮墙的声响。我裹紧被子,那声音越来越清晰,像是有人正顺着外墙往上爬。窗棂突然"吱呀"一声,有团黑影贴在玻璃上。
我抓过剪子,凑近一看,差点尖叫出声——那是张人脸,眼窝深陷成两个黑洞,嘴角咧到耳根,露出满嘴尖牙。它的下巴脱臼似的往下坠,滴着黏糊糊的液体,在玻璃上拉出银亮的丝。
"咔嗒"。
窗户被推开了条缝,冷风卷着湿冷的雨丝灌进来。那东西的手从缝里伸进来,指甲足有三寸长,泛着青灰色,指腹还沾着暗红的碎渣。我闭着眼乱挥剪子,听见"嗷"的一声惨叫,接着是重物摔在地上的闷响。
第二天我去村部找村支书,路过村东头的老宅院时,被个扎羊角辫的小丫头拽住裤脚。"姐姐,"她眼睛肿得像两颗红樱桃,"我家阿婆不见了。"
老宅院的木门上贴着褪色的黄符,门环上缠着一圈头发,发梢结着血痂。我刚要推门,门"吱呀"自己开了,霉味混着腥气扑面而来。
正厅中央摆着口红漆棺材,棺盖上用鸡血画着歪歪扭扭的符咒。墙上挂着幅画像,画中是个穿靛蓝粗布衫的老妇,脸上的皱纹深得能藏住蚂蚁。我凑近看,发现她的嘴角被画成了向上咧开的形状,像是定格在某个诡异的笑。
"那是陈阿婆。"身后传来声音。我转身,是昨天在村口见过的老妇,她怀里抱着个红布包,正是我前夜看见的那个。
"三十年前,陈阿婆的女儿难产死了。"老妇的声音突然变得很轻,像在说别人的故事,"她把女儿的皮剥下来,缝在自己身上。从那以后,她就能变成女儿的模样,在村里骗吃骗喝。"
我后退一步,撞在棺材上。棺材突然动了动,发出"咚咚"的闷响,像是有人在里面翻身。
"后来呢?"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。
老妇打开红布包,里面是团暗红色的碎皮,散发着腐肉的臭味。"上个月,她在村后头的水潭里泡澡,被水鬼拖了下去。可她的皮还在,附在谁身上,谁就会变成她。"
窗外传来孩子的哭声。我透过窗纸往外看,看见个穿红棉袄的小女孩蹲在雨里,她的脸——分明是画像上那个老妇的脸!
"那是春桃,"老妇说,"三天前失踪的娃。"
小女孩突然抬起头,她的眼睛里没有眼白,全是浑浊的灰。她咧开嘴,露出满嘴尖牙,朝着老宅院的方向爬过来。她的指甲长得离谱,刮过青石板的声音像刀割。
我转身就跑,却撞进一个冰冷的怀抱。抬头一看,陈阿婆站在我身后,她的脸正在融化,露出底下灰白的皮肤和密密麻麻的虫子。那些虫子从她的眼眶里爬出来,从她的鼻孔里钻出来,在她脸上爬成一张蠕动的网。
加拿大pc预测"女娃子,"她的声音像是从井底传来的,"陪阿婆待会儿好不好?阿婆好孤单......"
她的手掐住我的脖子,指甲刺进我的皮肤。我拼命挣扎,摸到口袋里的剪子,反手刺进她的后背。她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,皮肤开始大片大片脱落,露出底下蠕动的蛆虫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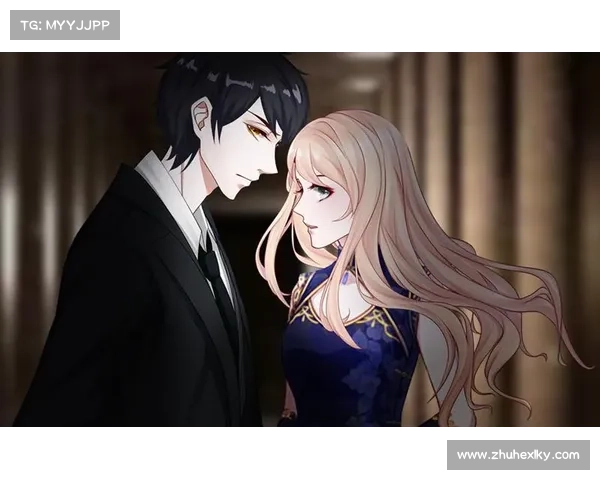
"你以为你能逃?"她的脸突然变成春桃的模样,"阿婆在你们每个人的骨头里,你们都是阿婆的皮......"
我猛地咬破舌尖,血腥味涌进喉咙。眼前的景象开始扭曲,等我再睁眼时,正躺在民宿的床上,老板娘正用湿毛巾擦我的脸。
"做噩梦了?"她轻声问。
我摸了摸脖子,那里有五道青紫色的指痕。窗外阳光正好,蝉鸣声里,我听见后山传来女人的笑声,细细的,像根针,扎进耳膜里。
那天下午,我在村志里翻到一段记载:"光绪三十年夏,青棠村陈氏女难产而亡,其母陈氏痛极,取女皮裹己身,自是村中屡现怪事......"
最后一页夹着张泛黄的纸,上面是用血写的:"莫信皮囊,莫信人面,人心比鬼,更会变。"
山风掀起窗纸,我看见院外站着个穿红棉袄的小女孩。她冲我笑了笑,露出满嘴尖牙。阳光照在她脸上,我分明看见她的皮肤正在慢慢融化,露出底下灰白色的......
是张老婆婆的脸。
第二章 旧疤
我是在第七天发现老板娘不对劲的。
那天我去村东头的老井打水,听见几个妇人闲聊。"上个月水潭里捞起具白骨,身上还穿着靛蓝粗布衫......""可不是?听说那骨架子的指骨弯得邪乎,像鹰爪似的。"
我攥紧水桶,想起陈阿婆说的"女儿难产而亡"。老井的水泛着绿,水面浮着层油花似的东西。我正要弯腰,井里突然伸出一只手,指甲三寸长,青灰色,抓住了我的手腕。
"啊!"我尖叫着往后退,水桶摔在地上,溅起的水花里,那只手已经不见了。
"姑娘,"身后传来老板娘的声音,"莫去老井。"她的手腕上还系着檀木珠,可我分明看见,她的指甲盖泛着青灰,和井里那只手一模一样。
那天夜里,我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月光透过窗纸,在墙上投下斑驳的影子。我摸出相机,翻看着白天拍的照片——村口老槐树下的老妇、村部的红漆棺材、春桃家的黄符。突然,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:民宿走廊的角落里,有个模糊的身影,像是穿靛蓝粗布衫的老妇。
我放大照片,发现她的后颈有道暗红的疤,和村口老妇的一模一样。
"叮铃。"
窗外传来风铃声。我掀开窗帘,看见老板娘站在院子里,仰着头看月亮。她的头发散开着,月光下,我看见她的后颈——那道疤正在蠕动,像条活物。
"老板娘。"我推开房门,"你后颈的疤......"
她猛地转过身,脸上挂着笑,可那笑比哭还难看。"姑娘,你看了不该看的。"她一步步逼近,我闻到她身上有股腐肉的臭味,和陈阿婆棺材里的一模一样。
"三十年前,我也是这么过来的。"她的声音突然变了,沙哑得像砂纸摩擦,"陈阿婆要找替身,我阿娘就把我推进了水潭。我在水里泡了三天三夜,阿娘的皮裹着我,才没被水鬼啃干净。"
她的指甲变长了,刺破我的手腕。"你看,"她举起手,月光下,她的指甲缝里嵌着暗红的碎渣,"这是阿娘的皮,这是春桃的骨,这是......"
"够了!"我抄起枕头下的剪子,朝她刺去。她尖叫着后退,撞翻了院角的瓦罐。月光下,我看见瓦罐里装的不是花,是半罐指甲,长短不一,泛着青灰。
"你以为你能逃?"她的脸开始扭曲,"阿婆在你们每个人的骨头里,你们都是阿婆的皮......"
第二天清晨,我在民宿门口发现了老板娘的尸体。她的后颈被撕开个大口子,皮整张剥了下来,挂在门框上,像面褪色的红旗。尸体旁边有滩血,已经凝固成暗褐色,上面用指甲画着个歪歪扭扭的"陈"字。
村支书来了,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,脸色煞白。"昨天夜里......"他搓着手,"我听见动静,想过来看看,可门从里面反锁了......"
我没说话,盯着他手腕上的疤——和老板娘、和村口老妇、和画像里的陈阿婆,都是一模一样的月牙形。
"陈支书,"我举起相机,"能说说您后颈的疤是怎么来的吗?"
他的脸瞬间白了。
第三章 水潭
村东头的老井旁有块青石板,刻着"止步"二字,字迹被岁月磨得模糊。我蹲在井边,用树枝拨开水面的绿藻,看见水下有团黑影,像是个人的轮廓。
"姑娘,莫看!"
我回头,是村口的老妇。她今天换了件靛蓝粗布衫,后颈的疤被头发遮住了。"阿婆,您认识陈阿婆?"
她叹了口气,坐在青石板上。"我是春桃的奶娘。春桃她阿娘难产那会儿,我在边上守着。陈阿婆抱着春桃的尸首哭,哭着哭着,就开始剥自己的皮......"
"剥自己的皮?"
"是啊,"她掀起裤腿,小腿上有道狰狞的疤,"她用碎瓷片割自己的皮,说要给春桃续命。血把地都染红了,我去拦,她一刀划在我腿上......"
我想起村志里的记载,陈阿婆的女儿是难产而亡,可春桃是失踪的娃。"阿婆,春桃不是陈阿婆的女儿吧?"
老妇的手猛地抖了抖。"春桃是我孙女,三个月前才满五岁。那天她去后山摘野莓,回来就不见了。后来有人在井里发现她的红棉袄,可尸首......"
井里突然传来"咕噜咕噜"的水泡声。老妇的脸色变了,她拽着我往村外跑:"快走!阿婆要找替身了!"
我们跑到村口时,看见村部的红漆棺材正在动。棺盖"咚咚"地响,像是有人在里面敲门。老妇突然停住脚步,指着我的脖子:"你脖子上......"
我摸了摸,那里起了个小疙瘩,有点痒。老妇尖叫起来:"是皮!阿婆的皮附在你身上了!"
我掏出镜子,镜子里的我后颈有块暗红的疤,正在慢慢扩散。那疤的形状,和陈阿婆、老板娘、村支书的,分毫不差。
"怎么办?"我声音发颤。
老妇从怀里掏出个红布包,正是我前夜见过的那个。"这是陈阿婆女儿的骨灰,"她打开布包,里面是些灰白色的粉末,"当年她剥了自己的皮,又想剥女儿的,被村民阻止了。骨灰能镇住她的皮。"
我们往村后头的水潭跑。水潭在两座山之间,水面泛着幽蓝的光。老妇说,陈阿婆的女儿就是在这里溺死的,她的皮就埋在潭底的泥里。
"跳下去!"老妇喊,"把骨灰撒在泥里,她的皮就不敢附你了!"
我咬着牙跳进水潭。水冷得刺骨,潭底的泥软得像棉花。我摸到块硬东西,挖出来一看,是具白骨,身上还裹着暗红的碎皮——正是村志里说的陈阿婆女儿的尸骨。
我掏出骨灰,撒在白骨上。突然,潭水剧烈翻腾起来,水面浮出张人脸,正是陈阿婆的模样。她的头发缠在潭边的树上,指甲刺进我的小腿,疼得我几乎昏过去。
"女娃子,"她的声音像是从地狱传来的,"你以为你能摆脱我?我在这村里三十年了,附过村妇,附过孩童,连村支书都是我的皮......"
她的手掐住我的脖子,我看见她的指甲缝里嵌着碎皮,和我在井里看到的那些指甲一模一样。"当年我女儿的皮没剥成,"她的脸扭曲着,"现在我要剥够一百张皮,凑齐她的身量......"
老妇突然跳进水潭,用红布包砸向陈阿婆的脸。"快走!"她喊,"我引开她!"
潭水把我往岸边推,我拼命游,听见身后传来撕心裂肺的尖叫。等我爬上岸时,老妇已经不见了,水潭面上飘着件靛蓝粗布衫,上面沾着暗红的碎皮。
第四章 真相
我在民宿的阁楼里躲了三天。
这三天里,村子里安静得可怕。没有鸡鸣,没有狗叫,连蝉都不再鸣叫。我透过窗户往下看,看见村支书在村口烧纸钱,火光里,他的后颈的疤正在蠕动。
第四天夜里,我听见阁楼的地板发出"吱呀"声。我抓起剪子,缩在墙角。门被推开了,月光下,站着个穿靛蓝粗布衫的老妇,她的后颈有道暗红的疤,正在渗出鲜血。
"女娃子,"她的声音很轻,"别怕,我不是陈阿婆。"
我举起剪子:"你是谁?"
"我是春桃的阿娘,"她流着泪,"我叫秀兰。三十年前,我难产死了,陈阿婆为了救我,剥了自己的皮裹在我身上。可她的皮是邪的,慢慢我就被她控制了......"
我想起老妇说的"春桃的奶娘",突然明白了:"你就是村口的老妇?"
她点点头:"我清醒的时候,就装成疯疯癫癫的老头子,怕被阿婆发现。可最近她的皮越来越强,我快撑不住了......"
"那老板娘和村支书?"
"他们都是被阿婆的皮附身的人。"她指着窗外,"你看。"
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,看见民宿老板娘站在院子里,她的脸正在融化,露出底下灰白的皮肤。村支书站在她旁边,指甲刺进她的胳膊,像是在吸取什么。
"阿婆的皮需要活人的精气,"秀兰说,"每附一个人,她的皮就厚一分。现在她要凑齐一百张皮,就能变成真人,永远活下去......"
"那春桃呢?"
秀兰的眼泪掉在地上:"春桃是阿婆的孙女,她不肯附身,就被阿婆杀了,埋在水潭里。她的骨灰能镇住阿婆的皮,因为那是干净的......"
楼下传来重物倒地的声音。秀兰的身体开始颤抖,她的后颈渗出更多的血,把靛蓝粗布衫染成了暗红色。"阿婆来了,"她说,"你快跑,带着骨灰去水潭......"
她扑向窗户,撞碎了玻璃。我听见她的尖叫混着风声,渐渐远去。
第五章 终局
我带着骨灰跑到水潭边时,月亮刚升起来。
潭水泛着妖异的红光,水面浮着几十张人脸,都是被陈阿婆附身的人。村支书的头在水里沉浮,老板娘的手抓着岸边的石头,指甲缝里全是泥。
陈阿婆站在潭中央,穿着靛蓝粗布衫,她的脸是秀兰的,是老板娘的,是村支书的,是所有被她附身过的人的脸。她的后颈有道暗红的疤,正在渗出鲜血,把潭水染成了血红色。
"女娃子,"她的声音像是有无数人在说话,"你带着骨灰来了,是来送我最后一程的吗?"
我把骨灰撒向潭水。骨灰落在水面上,发出"滋滋"的响声,像是落在烧红的铁板上。被附身的人纷纷惨叫起来,他们的脸开始剥落,露出底下白森森的骨头。
陈阿婆的身体开始崩溃,她的皮一块一块脱落,露出底下密密麻麻的虫子。那些虫子在水面上爬,发出"沙沙"的响声,像是秋天的落叶。
"你不该来的,"她的声音越来越弱,"我本来可以......"
"你本来可以做个好人。"我打断她,"秀兰阿姐那么善良,她不该被你利用。"
她的身体彻底崩溃了,变成了一滩血水。潭水慢慢变清,月光洒在水面上,映出我的影子。
我低头看自己的后颈,那道疤已经不见了。远处传来鸡叫声,东方泛起鱼肚白。
青棠村的清晨来了。
后来,我在村志的最后一页添上一行字:"陈氏女终,恶皮散于水潭,村人得安。"
离开的那天,我在村口遇见个扎羊角辫的小丫头。她手里拿着朵野花,冲我笑了笑:"姐姐,你是来采风的吗?"
我蹲下来,和她平视:"是啊,姐姐想听听青棠村的故事。"
小丫头歪着头:"那我给你讲秀兰阿姐的故事好不好?她是个好妈妈,救了很多人......"
山风掀起我的衣角,我听见水潭里传来笑声,清脆的,像银铃。





